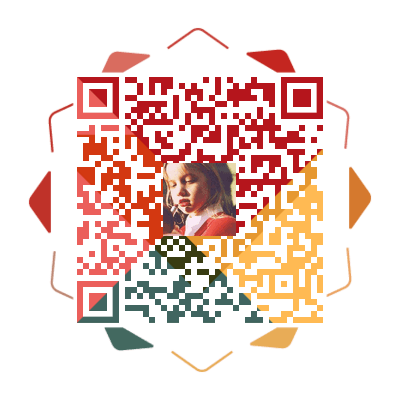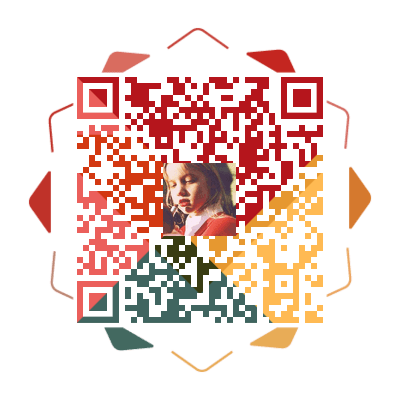为何发达给不了幸福?
为何发达给不了幸福?
Kenny《人类简史:从动物到上帝》勾勒认知革命、农业与科学革命,揭示虚构故事如何促成大规模协作,使智人主宰地球,也警示技术霸权可能反噬自身。
章节笔记:
章节1:认知革命
主要内容:人并不特殊。250 万年前,东非南方古猿演化出“人属”(Homo)。200 万年前,人属扩散至欧亚,因环境差异分化出尼安德特人等多个物种。然而,今天仅剩下了智人(Homo sapiens)。智人能够谈论虚构事物、相信共同的故事(如国家、公司、人权),这种能力使数百万陌生人协作,形成大规模秩序,从而产生了强大到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。从认知革命之后,智人就再无“原始状态”。所谓的“自然”,只是众多文化选项之一,人类历史,就是不断选择和混合这些选项的过程。
个人感悟:公司、货币、国家、考试分数……这些我每天拼命追逐的东西,原来只是集体想象。它们真实得让人不敢不信,却又脆弱得只要所有人同时“醒来”就会烟消云散。这让我不禁敬畏于,人类用故事就能调动亿万人协作,也警惕于自己可能被故事裹挟而不自知。现代社会把“人脉”量化为通讯录里的数字,可真正能提供情感支持的仍是那几十个熟面孔。原来这不是失败,而是大脑的出厂设置。与其焦虑“圈子太小”,不如珍惜眼前可触可感的真实关系。过去我常纠结“怎样活才够本真”。赫拉利提醒我:智人从来就在不断发明新的活法。想游牧、都市,都只是文化调色盘上的一抹颜色。关键不是“回到自然”,而是清醒地选择并承担后果。
章节2:农业革命
主要内容:农业革命是“人口增加、个人变惨”的奢侈生活陷阱。所有号称永恒、普遍的正义原则(阶级、平等)都只是人类集体想象的故事。要维持这套想象出来的秩序,人类必须用法律、教育、建筑等手段把它“写进”真实世界。帝国运转产生的海量信息,远超出人脑容量,因此催生了文字、档案与官僚系统。历史中,权力分配从来没有客观正义,聪明才智和社交技巧,往往比蛮力更决定地位。
个人感悟:我一直把农业革命想象成人类走向温饱、安定、文明的起点。赫拉利却说,那其实是一张越挣扎越紧的网——为了把更多卡路里锁进田埂,我们把更多自由锁进了谷仓。自己每天坐在格子间、盯着 Excel 表格,与烈日下挑水的早期农民并无本质区别。所谓“让生活更轻松”的技术,最终都成了让生活更复杂的理由。“人人生而平等”曾是我心中的自明真理。可赫拉利一句话就把它拉下神坛:那只是18世纪一批精英想象出来的故事,与汉谟拉比的“上等人/平民/奴隶”并无高下之分。这让我警惕——当我愤怒地指责某种制度“不正义”时,我手里的标尺可能也只是另一套人造叙事。人脑装不下帝国所需的全部信息,于是发明了文字、档案、算法。今天,我的生日、喜好、消费习惯被云端精确“记忆”,而我对这些系统却知之甚少。赫拉利提醒我:谁垄断了记忆,谁就垄断了定义现实的权力。当数据比我自己更懂“我是谁”时,我是否也正在沦为维护某套秩序的“生物载体”?书中最刺耳却也最解脱的一句话是:演化成功≠个体幸福。既然文明只是基因与模因的赛马场,我反而可以卸掉“必须参与宏大叙事”的包袱——不必把加班等同于进化使命,也不必将消费等同于自我实现。在承认一切秩序都是虚构之后,反而多了一点选择:我可以决定相信哪个故事、在哪部剧本里出演自己,甚至试着自己写一小段。
章节3:人类的融合统一
主要内容:
“自由”与“平等”在理念上不可兼得,法国大革命后两百多年的全球政治史,就是不断试图调和这对矛盾的过程。
人类大规模合作的两大工具:金钱:史上“最普遍、最有效的互信系统”,让陌生人也能交易。宗教(尤其是综摄):把彼此矛盾的思想、仪式拼接在一起,形成跨地域、跨文化的认同,从而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。
学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,而是意识到当下的一切——政治制度、经济秩序、种族关系——都不是“自然”或“必然”;一旦看清其人为与偶然的本质,就能想象并创造截然不同的未来。
个人感悟:“矛盾”。过去我常把自由和平等当成理所当然、可以同时最大化的“好东西”,却忽视它们内在的拉扯;把宗教、金钱看成“天然存在”的,却没意识到,它们其实是人类为了解决“如何与陌生人合作”这一根本难题,而发明的“补丁”。
赫拉利提醒我:
- 真正理解一个人或一种文化,不是去找他们“说了什么”,而是去看他们“说不通、做不到”的地方——那些让他们自己也左右为难的裂缝。
- “分久必合”不是命运,而是一连串人为选择的结果;今天被视作天经地义的价值、制度、身份,都曾是某个时代为了解决当时的矛盾而妥协出的“最不坏方案”。
- 一旦看见这些“人造”痕迹,我就多了份谦逊:我不必被现状囚禁,也不必对未来绝望——历史不是单行线,而是无数岔路的叠加。
换句话说,这本书没有给我答案,却给了我拆掉“理所当然”滤镜的勇气:先承认矛盾,才能想象新的可能。
章节4:科学革命
主要内容:科学发现,包装成符合社会价值观,或经济利益的叙事,才能被认可(如奶牛心理研究需关联“提高产奶量”而非印度文化中的神圣性)。
科学问题的优先级,取决于该项研究的资助者的个人偏好(商业利益、文化观念),而非纯粹的知识追求。
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(VOC)和西印度公司(WIC)的殖民行为(如建立纽约前身“新阿姆斯特丹”)说明,私人企业曾拥有远超国家的暴力与主权,甚至创造“华尔街”等现代符号。早期公司通过军事征服(如控制哈德孙河)追求利益,预示了21世纪企业权力集中问题的历史根源。
个人感悟:
读这两章时,我突然意识到:我们今天的“知识焦虑”,本质是被资本驯化的结果。
赫拉利笔下那个被迫更改研究计划的教授,让我想起自己——曾经为了申请课题,把“研究宋代女性诗词”改成“挖掘传统文化IP的性别经济潜力”;曾经为了投稿,把“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陪伴观察”包装成“养老产业情感劳动的盈利模式”。那一刻,我成了那个给奶牛喂抗抑郁药的科学家:我们不再问“奶牛是否痛苦”,只问“痛苦是否影响产奶”。
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故事更让我脊背发凉:华尔街的起点是一堵墙,这堵墙本是为了抵御原住民和英国人,最终却成了全球资本的象征。原来我们引以为傲的“金融中心”,不过是400年前一场暴力掠夺的副产品。那些被抹去名字的印第安人、被贩卖的黑奴、被剥削的殖民地劳工,他们的血早就被K线图的绿色掩盖了。
最刺痛的是:当我嘲笑17世纪荷兰人“为了胡椒杀人”时,低头看见自己手机里的钴(来自刚童工矿)、身上的快时尚(来自孟加拉的血汗工厂)—— 我们何尝不是21世纪的东印度公司股东? 或许真正的无知,不是“不知道”,而是只允许自己“知道”对利润有用的部分。当研究必须贴价格标签,当历史只剩胜利者的叙事,我们终会像那头忧郁的奶牛——吃着提高产奶的精神药物,却永远不懂自己为什么流泪。